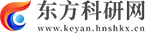架空/私设/全员恶人/不洁/玻璃碴里找糖/狗血虐恋/be/吃不消的大可爱出门左转,万分抱歉。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宫铁心忙起来的时候,陈一鸣就裹着厚厚的连帽羽绒服一个人无所事事的躲在楼顶的天台角落里望天。不知怎么,最近特别怕冷,而且总是很困倦,不想动,有些畏光。以前不是这样的。
连帽羽绒服是宫铁心的,陈一鸣自己除了制服和作训服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衣服。也不需要其他的衣服,在军部处理文件就穿制服,而作训服几乎适合一切场所,陈一鸣的活动简单至极,出任务,工作,顶多回来的路上绕个大弯去“栖音”给罗浮生买巧克力或者破天荒的去一次商场买生日礼物——当然,一年只去一次。公寓的柜子里整整齐齐的放着19个精致的小盒子,全都是没能送出去的礼物,每一份礼物都夹着小纸条,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Happy Birthday”,旁边工工整整的标注着具体日期,月份和日期整齐化一,只有年份一栏在逐年增长——给陈斯远的。面对这些永远也送不出去的礼物,陈一鸣心知肚明,却忍不住每年提前精挑细选的准备出来。看着囤积得越来越高的礼物盒,那些无处安放的感情好像也有了暂时的容身之所,不至于跟自己一样无家可归。
之前穿回来的井然的短袖还叠得端端正正的躺在柜子里,近几个月一连串的事多米诺骨牌一样压过来,不到最后一个骨牌倒下绝不会停止。对于未来,陈一鸣心里隐隐有种巨大的危机感,好在自己已经习惯了把那些恐、不安等负面情绪埋在心底,无论深海里怎样激流涌动,海面上都风平浪静一样。第一次有点为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产生一丝厌恶,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把衣服还给井然,也还没道谢,被林楠笙带走以后再没见过面,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林楠笙不会为难他吧,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只是偶然?
井然偶然出现在废弃工地里。
林楠笙的人也是偶然经过那里。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
陈一鸣双腿搭在墙体外,冷冷的看着远处黛色的群山,几只乌鸦在头顶盘旋,然后拍拍翅膀落在附近,漆黑的眼睛看着陈一鸣。
乌鸦。
陈一鸣想起幼年时期,还没被陈斯远捡回来的时候,总是在乌鸦口中夺食,有一只胸前一撮白色的羽毛尤为特别,自己总是抢它的吃的,说起来颇为不好意思,这样看起来其实乌鸦也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吧。许久没留意到那群乌鸦了,乌鸦寿命大概在13-20年左右,已经19年了,当年的那群乌鸦…看来也没机会报恩了,陈一鸣忽然觉得落寞得很也没用得很,心里乱糟糟的,索性仰面朝天躺了下来。落在高处乌鸦好奇的靠了过来,竟然正落在陈一鸣胸口。一人一鸟对视了片刻,陈一鸣笑笑伸出手试探着靠近,直到轻触到乌鸦的羽毛,胸口的小家伙一直没动,手指轻抚上乌鸦的脊背,触手生凉,漆黑油亮的锦缎一样,让人有点上瘾的感觉。
“呐,谢谢你们。我小时候多有冒犯,抱歉了。”
“没关系,吾看你可怜,故意给你的。不然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被你抢到。”
“哈哈,是吗,那还真是多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后一个字的音调因为过度惊吓被拐成九曲十八弯,陈一鸣手忙脚乱的起身,乌鸦拍拍翅膀落在他身旁,歪着头看着他。
“人类,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确定四周没人,陈一鸣浑身僵硬的转过头看着眼前的乌鸦,“是…是你在跟我说话?你怎么知道以前的事,你是我小时候那…你会说话?!我是做梦吧,对,做梦…”陈一鸣使劲儿掐了下自己的脸,很痛,乌鸦还在歪着头看自己,没…没醒?!陈一鸣又使劲儿掐了下脸,脸都掐红了,乌鸦还是在看着自己。
“人类,在吾面前这样失礼,念在你身体抱恙的份上,不与你计较!”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息。
“你才有病呢,我!…我…”陈一鸣的眼睛黯淡下来,“也许你说得对。”
“人类,你活不了多久了。”
陈一鸣怔了怔,“我知道。我只希望在那之前,来得及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完。”
“人类,你从那个人类的实验室里出来以后整个人的气场就变了,你身体里被硬塞进了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吾说不好,用你们人类的话应该怎么说,其他的人格?”
那不就是精神分裂?陈一鸣闭了闭眼睛,再睁开的时候眼睛已经变成紫红色的竖瞳,“像这样?”
乌鸦惊恐的拍打着翅膀,踉踉跄跄往后退去,一屁股撞在身后的隔离墩上趴在地上狼狈得很。陈一鸣伸出一种以牙还牙的快感,“不好意思。”手伸向面前的乌鸦,乌鸦却连连后退着缩在隔离墩后面,连自己有翅膀这件事都忘了,“人类…别过来!”
“嗯?”陈一鸣收了自己红色的竖曈,又变成了异色瞳,“这样可以吗?”
乌鸦探出身体,松了口气一样,“人类,你刚才的样子满身戾气,还有另外一种吾不太能表达清楚的东西,像是…像是血脉里的什么东西要觉醒了散发出来的威压一样,吾…竟然有种想要跪拜的冲动。嘁,区区人类,妄动神明是要受惩罚的。”
“这世界真的有神明存在吗?”乌鸦跳上陈一鸣的掌心,陈一鸣伸出手指轻抚着乌鸦的脊背,眼睛却望向远方。
“哼,愚蠢又自负的人类。”
“乌鸦嘴都这么硬吗?”陈一鸣笑笑,伸出手指点了点乌鸦的小尖嘴,“我只知道乌鸦嘴预言坏事的时候挺准的,原来还这么硬,怪不得不讨人喜欢。”
“区区人类,不得无礼!谁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怀里的乌鸦炸开羽毛,身体看起来圆了一圈。
“你陪我一会儿好吗?”困倦得很,不想一个人睡过去。
“人类,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行吧,吾答应陪你,区区人类,哼!”
……
“你叫什么名字,”陈一鸣就地躺了下去,“我不能总是叫你‘喂’吧?”
乌鸦拍拍翅膀飞上陈一鸣额头,“人类啊,膜拜吾吧,以王之名尊称吾吧!”
他妈的中二货看来是没少看电视,这都跟哪儿学的一嘴混账话,陈一鸣把头顶的乌鸦抓了下来又放进怀里,“哦,你好黑煤球。”
“吾名烟墨!”
“淹没?”
乌鸦一爪子就要抓上陈一鸣的脸,被陈一鸣伸手很轻的挡开,“不逗你了,墨色烟华,光彩闪耀,很适合你的名字。”
“哼!区区人类!知道吾的名字就是吾的子民了,吾等会护佑你的。”
中二鸟,陈一鸣在心里暗自吐糟了一句,不过难得有人…有鸟陪自己说说话,这样也很好,“那请你多指教了。”
醒来已经躺在宫铁心办公室的小床上,宫铁心正把几个血包放进冰箱冷藏室里,回过头看见陈一鸣醒了,走过来蹲下身摸了摸他的额头,“怎么在天台上睡着了,还好我回来得早,不然你要被冻死在外面了。”陈一鸣看向窗外,片片雪花在风中飞舞着飘散,“对不起,感觉浑身发冷,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我看你是要冬眠了。”宫铁心递过血包给陈一鸣。
“冬眠???”
“你现在除了没有鳞片,跟一条蛇没什么区别,白娘子知道吧,修炼了1000年,你嘛,”宫铁心给了陈一鸣额头一记暴栗,“差远了。”
陈一鸣捂着额头可怜兮兮的看着宫铁心,“对了宫医生,我刚才…在天台遇到一只会说话的乌鸦。”
宫铁心给了陈一鸣一记暴栗,随后又试了试他的体温,“乖小孩你做梦了吧?还会说话的乌鸦,真以为自己是美男蛇呢。快吃,饿了一天了吧。”
陈一鸣把血包放进嘴里咬开,冰凉的血涌进嘴里,腥气冲天却不能不喝,如果不喝的话自己说不定晚上就要去咬人了,“大概是我做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