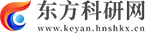其实,杨遥还是写这一类型的小说写得最好。或许是因为杨遥那种诚实、憨厚、略微伤感的气质与此类型的小说格调相吻合;或许是这一类型的小说写的就是杨遥自己,写的就是杨遥的心境、内心的伤感与失落,以及那些永远都无法化解的纠结。杨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沉思者。杨遥是一个憨厚、老实、可爱的时代失败者的讴歌者。其歌兮,总是有淡淡的哀伤,戚戚的悲怀。其歌者,总是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望着满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望着遥远的远方,目光里荡漾着心中永远不可言说的渴望、焦虑与紧张。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他们或许本来就不是对权力都多么大的渴望。他们只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与勤劳刻苦,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实现自己心中理想的目标。他们只想依靠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应有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权利,过上相对好一点的生活。但是,现实生活却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点小小的心愿。
《把自己折叠起来》(《收获》2023年第3期)的舒文、孙林和李老虎都是三个这样的人。
舒文和孙林是高中同学。舒文和李老虎是小学同学。舒文虽然靠自己的努力是到了省城工作了,但总是事与愿违,本来原先答应的是两三年后不再让他写材料了,让他去干他所爱的专业工作。但是,五六年过去了,依然还是让他写材料,做事务性的工作。有时忙得高中老同学到省城办事想见面吃顿饭,他却正在为下午开会汇报工作的领导写讲话稿,“实在走不开”。正好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单位想调他去“专心搞专业”,他这一段时间正在纠结于此,就是去还是不去。
孙林也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上来的,先是在“另一个乡镇当乡长”,现在是在舒文和李老虎所在的乡镇当书记。工作繁忙而复杂。忙得大年初二的晚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的聚一聚,聊聊天,喝点小酒,松驰松弛平日里总是高度紧张的心。但是,先是张县长的电话打来了,“让我明天陪他去省城办点事”。一会儿,又是县里的刘书记打来电话,“明天市里检查组要下来明查暗访春节期间纪律问题,还有个森林防火督察组也要下来,刘书记叮嘱我哪个乡镇是重点。”舒文是理解孙林这些看似风光其实内心苦楚的人,他“想起孙林明天还要陪县长去省城,为他头疼起来”。所以,像孙林这类型人无形之中养成了仰望权力又恐惧权力的人,“他脸上都是笑,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夹着,屁股往下坠,裤子褶了起来,像那儿有条尾巴似的。”其实,此时,电话里传出来的是一个“威严而柔和的声音”。
李老虎大年初二晚上吃饭聚会最普通、最卑微的一个人。五年前,舒文在火车站碰见他和他妻子时,他是靠每个月到周边赶庙会“套圏圏”为生。今年年前腊月二十九,舒文在车站碰上他时,已经是在赶庙会“开碰碰车”了。可是“疫情爆发”,害得“不让人群聚集”,挣不下多少钱。他“为了不能让人小瞧他”“更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加之“这几年我在社会上闯荡”,增长了才干,所以思思谋谋想当“村委主任”。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受苦人”,而舒文是在省城机关部门工作,是“城市人,领导”,一再求小学老同学帮忙,和舒文的高中老同学孙林说一说。他还大年初一跑到舒文家给他的父母亲拜年,央求舒文把当乡镇党委书记的孙林约出来,他请客,吃顿饭。李老虎坚信“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英雄,另一个是当村长。为了当英雄,我还专门到少林寺练过武术”,但是,“咱们生在太平盛世,很难当英雄,我就剩下一个理想了,当村长,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主任”。他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官,在这个职位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为了准备和吃这一顿饭十分用心和用力。总是想讨好今晚吃饭的所有人,总是想在今晚吃的这顿饭中,尽心尽力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诚心,尽心喝酒,尽力去表演节目,展现他的“少林绝技”,“把两只脚勾到脖子上”。可是当乡镇党委书记的孙林却两次出去接电话,打断他的真诚表演。他只好三次去表演这个高难度动作,也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和高潮,三次去“把自己折叠起来”,尽管“他的骨头啪啪地响”,脸“涨得通红”,“像在刚才喝酒涨红的脸上又涂了层漆”,他“终于成功地把两只脚勾到脖子上,团成一个球状的样子,翻出来的脚掌上穿着白袜子,白得耀眼”。但是,高难度动作是完成了,“正在他得意时,忽然椅子被压塌了。随着惊叫声,李老虎摔倒在地上。”大家惊叫着围过去看他时,他的一条腿还在脖子上。孙林紧张地说:“赶紧去医院吧,检查检查有没有事情,我医院有熟人。”他却摆着手站起来,一再说没事,没事。其实他的腰是有点受伤了。因为正月初五他到火车站送舒文到省城,“一手扶着腰站着”,舒文“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你回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他“立刻把扶着腰的手拿开,双手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说没事,没事。我忽然想起他在那天晚上第一次“把自己折叠起来”的时候,“裤子口袋里忽然掉出来一堆东西,打火机、两张银行卡、身份证、一串钥匙,还有一叠钱。”我也和小说中的人物舒文一样,“心里一颤”。这或许可能就是当农民的、一直在靠四处赴庙会挣点小钱的李老虎的值钱的全部家当了。
“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可能就是小说中人物李老虎、舒文和孙林心中的真理。这也可能是现阶段大多数人心中的真理。为了实现心中的真理,他们都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地方,不得不“把自己折叠起来”,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虽然身份、处境不同,生存状态不同,但是,他们都缺乏自立、自主、自信的状态。他们虽然都在积极的向上努力,有理想,有希望,却总是在现实面前表现得无可奈何,不能圆满地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他们有积极向上的自觉,但四周存在的却是自觉向上努力的种种局限。
杨遥的这一类型小说,总是多少具有一种寓言的性质、哲学的味道。人,存在于两个世界之中。一个世界是自己“个体生命”的世界,一个是个体生命对应着的“存在世界”。这两个世界,互相独立,却是又互相依存。作为个体生命世界里的人,总是想努力突破目前的生存状态,争取更好的、向上的一种生存世界。但是,另一个好的、向上的存在世界,虽然没有拒绝那个个体生命的世界,但也总是不能形成充分的交流沟通。两个世界之间形不成应有的理解、同情和帮助。这就让那个个体生命世界更难把握和了解自己。这成为人心中永远难以化解的纠结。所以,读杨遥的这一类型小说,总是感到心中失落,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痛,产生一种淡淡的伤感和忧愁。但是,杨遥的这一类型小说,尽管总是让人有些伤感,却在这种伤感中,总能淡淡地流露出个体生命世界的美好和存在世界的希望。当然,在这两个互相独立又依赖的世界里,还是依然存在一些局限与遗憾的。
读杨遥的这一类型小说,总是让我想起了契诃夫。正如阿姆菲捷阿特罗夫所说:他总是“把巨大的才华、敏锐的才智、明亮的灵魂和无限的仁慈结合在一起”(转引自顾春芳《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第008页),他的小说总是一切都真实可信,又一切都恰如其分,让我们去理解和懂得个体生命世界与存在世界之间的自觉与局限,告诉我们:“唯有躬耕自己的土地,诚实地劳动并创造,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断绝关系,懂得珍惜和体验每一个美好的当下。”(同上,第098页)不管这个存在世界是多么令人伤感,我们需要做的,依然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其他的不用去操心。”(同上,第189页)契诃夫内心深处的真挚、淳朴、亲切、温柔敦厚、富有同情心,让人终身难忘,正如他给他的女友丽季雅·斯塔希耶芙娜·米齐诺娃的信中所言:“我热烈的爱着的,不是你”,而是“在你身上我过去的痛苦和逝去的青春”。(同上,第187页)
杨遥的这篇短篇小说,依然要表达的是他一贯要表达的,对我们普通人面对“过去的痛苦和逝去的青春”的伤感与失落。人的一生,能有几个青春啊?人何能不去为此伤感与失落啊!
2023年5月28日写于山西孝义
关键词: